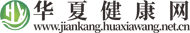万年无归
文/朝朝
奶奶是世上最后一位百岁老人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她个头不高,不到一米五,体胖,像个老年版的年画娃娃——倒不是生病,而是她的胃口太好了。大抵是早些年饥荒时烙下的病根,掉光牙齿也不影响干饭,自有强大的胃液辅佐。
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,父母辈忙于工作,有时春节都不回家过年,把我们交由奶奶看管。奶奶胃口好,厨艺却不怎么好,看我们吃饭慢,或是吃的少,就会叨叨着“快吃!怎么学得跟乌龟一样!”
托奶奶的福,我大表姐长成了她的翻版。二表哥倒是长到一米八,体重则加倍到二百多斤……我也胖,不过是小时候,后来我的基因被挑中,送去上学,又因为身心素质良好,被培养成专业跳水运动员。
我的跳水成绩一般,没什么身价,不过只要是女人,身体都可以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。且放心,即使是在文明高度发展的2145年,即使是在人类迈入永生时代的关口,仍会有部分人愿意肩负繁衍的重任。
2050年,年关至,政府通过了关于《原生人体(无限)修复改造》的提案,于是那几年,街上经常出现当街拐卖人口的乱象,甚至生抢,男的女的都要抢。
他们都疯了,生怕自己绝了后,不惜犯罪也要抢到好基因。他们这么做也有他们的道理,若能顺利生下基因优良的孩子,便可将功折过,留下一条性命。
铤而走险的人很多,老实人更多,大部分老实人生活窘迫,既没钱,又身娇体弱,只能拖家带口跪在繁华街上苦苦哀求,求路过的好心人将自身的精子或卵子献出来,造福下一代。
当然,后者通常会以“影响市容”等罪名被警员逮捕,有时遇到脾气暴躁的警员,还会被当街暴打一顿,严重者还会被拖走实施物理阉割。
这两种情形我都见过……起初我还会驻足看一会儿,后来也见惯不惯了。饶是如此,求繁衍的人也只多不少。尤其是每年春节左右,一点零星的灯火和烟火,也似烧在他们的神经上,不断加深着灭亡的恐惧。
我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运动员,除非必要,一般不会上街溜达。
身为女运动员的我,每次上街都会被无数双眼睛盯住,甩都甩不掉。有次遇到胆肥的,一伙人围堵我,试图将我拖入无监控的小巷子里……
结果,自然是打不过我,报警求助。
次数多了,负责记笔录的小警员对我颇为同情。
“这个月第几回了?”
“这月还是第一回。”
“你这次下手有点重,要被关十天哦!”
“唉……行行好,我家里还有独居的老人,我得回去给她做年夜饭。”
“家里地址给我。”
警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警局系统的监控,他必须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,不过出于好心,他将我单独拘留,还替我去给奶奶做了饭。
十天后,他亲自驾车送我回去。
我已经十天没说过话了,他有些担心我的精神状态,对我百般殷勤。我知道,他也贪图我的身体和体内的基因,区别在于他看着比他们更善良一些。
临下车,我才开了口:“下周六吧,民政局等我。”
我没说定时间,忘了,小警员就在民政局眼巴巴地等了一天,直到我出现。
我来晚了,他好脾气的没有发火,带着我赶在当天民政局下班前的最后一刻钟登记成功,还特意去领了份电子结婚证。
他展示电子结婚证给我看:“你知不知道这意味什么?”
我想了想,告诉他:“这意味着,以后他们不能再觊觎我的身体了,因为我有正义的打手。”
他笑了两声,点头应下:“哈哈,好。”
我生来不爱笑,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好笑的,经常惹得他犯笑。
“咱们先说好,若是以后我再遇袭,你得允许我先揍他们一顿。”
“你是跳水运动员,不是拳击运动员。”
“好吧……那你得保证替我狠狠揍他们,以后见到我就绕道走。不,是见到女人就绕道走!”
“哈哈哈,你说话真逗……”
奶奶和爷爷是两小无猜,青梅竹马,两人奉子成婚,生下我大伯,之后接连生下我姑姑和我爸。怀我爸的时候,爷爷在国防前线牺牲了,奶奶没舍得打胎,也没再嫁,一个人将三个孩子拉扯大。
奶奶说,婚姻就是一张纸罢了。
她是忠于爱情的。可惜现如今的婚姻连张纸都没有,只需要拿着身份ID,在现场采集一点血液、最后再同意一份三十页的婚姻声明,就有了所谓的“爱人”。
爱人是旧时代的称呼,电子结婚证也是旧时代的仪式感。
我丈夫喜欢称呼我为“爱人”,好像我们是因为爱情联结的。可聪明人都看得出来,重建世界的阶级已然固化,贵族交配贵族,精英交配精英……或许底层人之间会产生爱情吧?但除了他们自己会傻到歌颂苦难外,根本没人在乎,就如同没人在乎他们的命。
或许你看到这里会疑惑,那些迫切需要孩子的人类群体,为什么宁愿去骗、去偷、去抢——宁愿触犯法律,也不选择找人结婚?明明结婚登记听起来不是件程序繁琐的事。
对不起,我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运动员,回答不了。
许多年前,地球爆发过一场漫长的饥荒,据说是由病毒引起的,随风飘散在全球各个角落,导致人类大量衰亡。
如今全球所剩人口不足十亿,我所在的国家,人口算多的,剩八千万。
灾后重建的世界是残酷的。作为人,首先会因健康区分为两大类,体内检测含有朊病毒的人,会自然地被社会和人群歧视,最终以各种想得到和想不到的残酷形式,走向死亡。健康的人似乎更惨,他们见证着身边无数人死亡,每日活在未知的惶恐之中,要么麻木,要么疯狂。
如此,那些拥有健康的、优良基因的人则更显尊贵,不过他们维持的体面——如婚姻,也是关乎利益,无关生育。
运动员是第一批接触《原生人体(无限)修复改造》实验的人,我的比赛成绩不算好,但身体素质综合分最高,有幸入选第一批接受实验的人员名单。再准确点说,我,编号97045,是接受原生人体(全)改造并顺利存活的首位女性。不幸的是,我同时是唯一一个经历此手术还能存活的人类。
当然,这是后话了,在被推进手术室前,没人知道谁能活着再被推出来几次。
我亲爱的丈夫,他为此担心我,在我被推进手术室的前十分钟,他放弃了参与一次重要的抓捕行动,选择留在手术室外陪我。
我再次提起奶奶,我唯一在世的亲人。
我们家从来都不是幸运的,在我服役期间,偌大的一个家除了奶奶,都死了。有被战事波及的,有因工作猝死的,还有出意外没救下来的……总之,最后只剩下我的奶奶。
“亲爱的,如果手术失败了,请你把小乌龟交给我奶奶。”
“不行。”他当场拒绝我的哀求,“那是咱俩一起救养的小乌龟,你没权利单独处置。”
好吧……
为了让奶奶能吃到我做的年夜饭,我会努力活下去。
现在,我依然活着,故事讲到这里显然不能结束。
第一场手术很顺利,医生从内脏入手,先把我的一个肾替换为人造肾,再把我的一个肺片替换为人造肺片……这次手术过程不到三小时,但要想全身改造,至少需要三十年。
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,我基本告别了运动员生涯。
“亲爱的。”我总这么唤我丈夫,“我很好,你不用在家陪我。”
我术后需要卧床修养,他则一身家居服,在家里和机器人抢打扫卫生。我一劝他,他就躲在卫生间里人工洗刷小乌龟的壳,装听不见,好像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执勤工作,冠以“爱人”的名头。
我不跟他辩,小乌龟原本是我救养的宠物。
当年那场病毒除了危及人类,还造成了百万种动植物的灭绝,只有海洋动物大部分得以幸免。在海豹,海豚,水母及诸多鱼类中,乌龟是当前人类养得最多,也最好养的动物。
我们养的是玳瑁龟,龟壳一米多,体重近200多斤,体型不小。我们之所以叫它小乌龟,是因为它有千年寿命,养时还不到30岁。
多有意思,再往后三十年,小乌龟长到60岁时,我的生命体征还是30岁。
此后不到十年,随着人体改造技术的实验在我身上接连成功,这项手术正式面向社会。渐渐的,街上很少再出现十几岁的年轻人,最年轻的人都是三十岁。
这世上的新生儿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。
我在进行子宫摘除手术后,曾劝丈夫接受人体改造手术。他原本比我小几岁,但我40岁那年得以换皮,模样还维持在30岁,他却老得好像快50岁了,顶着中年人的疲态,始终不肯做手术。
他在警局的同事们,大多都已接受改造,有甚者已经在体内装上武器,并以此立功——警员原本是这项技术的第二批受众群体,但现在司法体系里,唯独他还是原生身体,职位升不上去也就算了,还积攒了一身伤。
印象里,那是我们唯一一次吵架。
至于是从哪句吵起来的,吵的内容是什么,吵到最后是个什么结果,我都记不大清了……我根本就不在乎,如同我根本不记得他的名字。
不过我一直牢牢记得他当时吼我的那句:“你真是个怪物!”
我承认,自己当初没有上报就选他作为结婚对象,只是为了找个人给替我给奶奶做年夜饭。如今承认了也没什么不好,我不会因为他的咒骂而感到一丝伤心,各种意义上的,因为接下来的手术还等着换掉我的心脏。
我这颗心,是爱,是恨,是怨,是忧,也就两年到头了……
两年后,我被换掉了原生的心脏。手术很顺利,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人造心脏在胸腔里有力地跳动着,尽管没什么温度,有些冷,但好在没有严重的排异反应。
按医生所说,这项实验性手术是不建议运动员换心肺的,因此我彻底从篮球队退役……不用为我的前途惋惜,当身体有99.99%的改造成功率时,人就不需要再打球,也不需要再努力,我仅是站在春晚舞台上,像正常人一样说说笑笑,就足以成为最瞩目的明星。
唉,到最后,我还是成了出卖身体的女人。
等等,我这并不是自怨自艾。我知道,医院外还有太多人想出卖身体来获得钱财,不止女人,不止男人。和他们相比,我似乎又是幸运的,毕竟他们耗尽一生好不容易凑够做手术的钱,却基本都死在了手术台上。
细心的人会发现,原生体改造的手术定位一直是【实验】。
我是完美案例,完美到谁都称赞我,似乎我生来就是为这个实验而生的。而他们——那些可怜的人们,包括为我服务的科学家、医生们,他们都会用羡慕的眼光扫视我全身上下每一寸。
一开始,我厌烦这种目光,如同我厌烦我的丈夫。但随着时间对我的治愈,我逐渐对这一现状释然:这世上,有太多想伴我同行的人和事,他们或难以察觉,或大声宣告,或暗中较劲,但结局都是一样的——在日后的某次术中或术后,因为各式各样的问题死去……
唯我永生。
真可怜。
根据2075年统计,每三个人中,至少就有两个人都接受过人体改造实验。在政府单位,职工则被强制执行人体改造技术,而随着警员中的人体改造率暴增,城市犯罪率的逐步下降,人体改造实验竟成了近十年来频次最高的死亡原因。
当城里发生本月第二十四例命案时,我刚做完面部手术,在一片漆黑中,我用新安装的耳朵捕捉到了丈夫的死讯。
他是自杀的,抱着我的小乌龟,从我经常仰望星空的天台跳了下去……前天夜里跳的,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今天早上,肉体摔得稀巴烂,没有一起科技的成分。
他是故意自杀的,我知道,他生前表态过,极不希望我整容,可作为人体改造这项实验的全球代言人,这个手术我必须做下去。
为此我曾向他保证,立下合同,哪怕他坚持原生体,老到一百岁,我也依然爱他。
结果他还是恨我,恨到不仅要带走一个无辜的生命,还要写下遗书,向这个世界昭告我及这项实验的罪行。
医生对我严加看管,第一时间没收了那封遗书。其实他不必紧张的,双目暂且失明的我,只能哀求:“可以念给我听吗?”
“不,你的眼睛不能哭。”
不想哭和不能哭,到底谁更残忍?
我彻底丧失了哭的权利。新眼球有着不输人眼的超高清度,可以透视物体,可以扫描文件,可以远望星空,可以拍下无数瞬间……可以装下这世间所有一切,却无法流泪。
而我的心,只能滴几滴油以示悲痛,还不能滴太多次,不然会像频频短路的廉价机器人。
“还差脑子。”我听到医生说,“只要把你的大脑升级,你就是世上第一例成功经受全身改造的人类了。亲爱的,你会名垂青史!”
医生比任何人都想名垂青史,可怜的是,他的体质仅能支持很低级的改造,而我是他的希望,他的成就,他的未来,是独一无二,无可替代的存在。
这样的我可以提出条件。
我求医生救救小乌龟——那具壳裂开而已,它的肉体还活着,只要医生肯造一个假壳子,它就能活下去……它能活!
我的这份坚持让医生有些无奈,但他还是抽时间为小乌龟做了手术。幸运的小乌龟,荣升为世上第一例原身改造的乌龟,绝对配得上世界第一例全身改造的女主人,名垂青史。
活到这个份上,人不是人,龟不是龟,欲望还是欲望,满载名利的桨,谁也不知道这艘时代的巨轮驶向何方。
丈夫死后的第五年,我迎来了全身改造的最后一步——换脑。医生用仪器拷贝了我大脑里的全部记忆,拷贝过程中的电流“滋滋”过脑,让我神思恍惚……缓了好久,我才重新听到医生的声音。
“97,你先回家吃年夜饭吧。”
准备工作已经做好,医生对操练许多的换脑手术没了把握,他一紧张,我这个躺在手术台的更紧张,速速从医院溜了。
我还记得回去给奶奶做年夜饭。
她已是世上为数不多的老人了,临近百岁,头上已布满银发,圆润的脸庞爬上抬头纹眼角纹法令纹……不变的还是那双眼,慈祥中透出对陌生世界的疑惑,却依旧逢人就笑,眉眼好似一对月牙儿。
她太老了,老得有些痴呆,庆幸的是“尊老”那条传统道德还没被彻底摒弃。当然,有我守着,谁都不能苛责一位百岁老人怎么还活着。
“你是谁呀?”
“我是您孙女呀!”
“我的宝贝孙女!放学啦!”
“我都退休啦!”
“退休啦?你多大啦!”
“过了年就56岁啦!奶奶!新年快乐!”
忘了?没关系的!我们会重新认识,一遍又一遍。记忆也许会遗失,但她总会凭借心底的熟悉感认出我来。她的心只是老了,不是死了,时而反应慢着,时而反应快些,总归一次次地认出我了。
世人渴求永生,不惜舍弃陪自己长大的一身筋骨血肉,殊不知血脉延续,才是人类维系永生的最优解。
“你是谁呀?”
“我是您孙女呀!”
“我的宝贝孙女!你今年多大啦!”
“过了年,就156岁啦!”
“哎呦!胡说呢!”
“是真的呢!我没骗您呢!”
当初的换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,太过顺利,以至于我眼看着医生化身为嫉妒的魔鬼。不,或许说是种凌辱更为贴切。
无论经历多少年,我自始至终都将自己视为人,活生生的女人,并且从未因此性别而后悔。反观医生,一个见证我成长,与我相处最久的异性人类,却早早迷失了最初的善良,将我视为他的机器、商品、个人所有物……
他抱着我哭:“你知道断臂的维也纳吗?那是古代最了不起的艺术品,你应该和她一样……对!我得毁了你……”
太晚了。
我的大脑已经开始接收到信号,那个信号于我的感觉无比熟悉,就像是未来某个时间段的自己发来的:你还在等什么?
我忽然就有了伸出手臂的力量——放心,我不是为了献出男人口中的美,而是为了终结这场生存游戏。
我将医生抱在怀里,抚摸他的头,直到扭出一声清脆的“咔吧”声,恰恰好盖过那声“谢谢”。
在遥远的西方故事里,维纳斯是从海里升起的女神:
“世界之初,统管大地的该亚女神曾与统管天堂的乌拉诺斯结合,生下一批巨人……
后来,夫妻二人反目,该亚女神盛怒之下命小儿子克罗诺斯用镰刀割伤其父……
当乌拉诺斯身上的男根被斩落大海,激起千层泡沫,代表爱与美的维纳斯从中诞生了……”
我从不喜欢这种西方故事,后来才知道,原来我是不喜欢“女人在哪里都一样”。
“那天,你站在刺眼的灯光后面,问‘谁愿意相信你’,问了三遍,结果只有我肯从女子队里站出来……你们不知道,那天我也偷偷问了自己三遍‘谁愿意相信我’。”
医生睁大一双眼睛,满是不可置信,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我。我勾起嘴角,在双臂松开他冰冷扭曲的身体前,抬手,用指尖轻轻合上他的眼皮。
“恭喜,您创造了一位新神。”
医生到死恐怕也没意识到,他信错“人”了。于我而言99.99%成功率,于其他人,就是99.99%的死亡率。然而他从没怀疑过,也不屑去问,97045生而为女人的意义究竟什么。
我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,不好回答,但我可以用漫长的岁月专心想一件事:编号太长了,我需要一个好听又好记的名字。
据奶奶回忆,她曾经是有名字的,三个字,但因为已经有太长时间没有人唤过她的名字,她近乎忘记了。不过我可以悄悄告诉你,她叫“淑英”。
年轻时,淑英的活力就比一般女人还旺盛,她可以一天打五份工养活自己和三个孩子,到老了也可以养活三个孩子的孩子,是家中的主心骨。然而,如今她愈发年长,身体各项功能逐渐衰退,没有一处符合人体改造手术的条件,唯一可以留存于世的记忆也因阿尔兹海默症残缺不全。
我太想太想太想太想留住她了。
于是我绞尽机械般的大脑,努力想到一个方法,就是将所有关于淑英的记忆搜集起来,不论是我自己脑子里的,还是幸存人脑里的,哪怕只有一声招呼,一次笑脸,我都没有遗漏,一一搜集,再结合之前留存的所有关乎淑英影像资料,一并投喂给小乌龟的壳。
“你是谁呀?”
“我是您孙女呀!”
“你多大啦?”
“不知道……这世人只剩您和我了,没有新年了。”
“我是谁呀?”
“您啊!您是这世界……最后一颗人心。”
万年流转,沧海桑田变迁,小乌龟化身最忠诚的使徒,乖乖地驮着那颗心,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前进……为了留住这颗心,我会晚小乌龟一百步出发,以求在有限的时间里无限地前进、前进、再前进。
直到长河流至大海,大海干涸,小乌龟再也游不动……
我想在海的尽头点燃一把火。我也确实这么做了,在海浪依旧拍打礁石的地方,寻处沙坑,将小乌龟和它的壳——我奶奶的灵魂——我的心在熊熊大火中融为一体。
火葬是古老的死亡仪式,我不懂,不过转身间,眨眨眼,竟意外地造出了新物种。
该怎么形容它呢?它和那封染血的遗书极其相似,身上无一处不在散发死亡的腐朽。也和那把染血的手术刀一样令灵魂胆颤,需要吃很多很多顿年夜饭也能填补残缺的躯体。
哦,我忘了,没有新年了,我都忘了年夜饭的味道。
我还是不爱笑,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它,看着它那些体肢以非常规的方向扭动,努力靠近我,那层坚硬的躯壳向下分泌出黏黏的血水……
只有敢于直视恐惧的人才会发现,那壳肉间不断剥裂再生的地方,有块口器,正靠不停蠕动尝试发出声音。
其实它什么都不用说。
它不死,我便陪它。
它活着,我便爱它。
无条件,如同爱我自己。
“您好,我叫97045,是名跳水运动员,我今年……不好意思,我活太久,很多事记不清了……
不过我记得从前总有人说我是‘死怪物’。
呵,确实,我不够美好,所以我打算最后跳一次海,将旧世界的秘密沉入海底。
而你,亲爱的——
这是我赋予你的新世界!
祝你新年快乐。”
-end